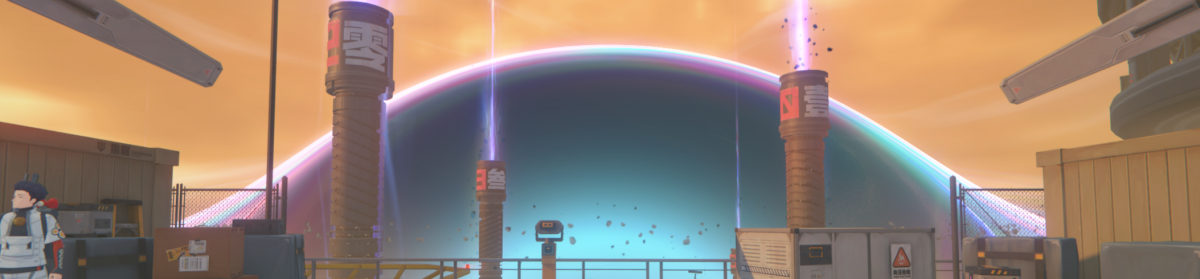ref.
https://www.facebook.com/makotomoto/posts/1053392444678559
陳真的雪若巴勒斯坦網沒有辦法有系統的查找資料,只能放在這邊了
(陳真 | 2015.08.02 03:24 | #)
柯恩兄弟在 “一個正經好人” 裏頭有句話說道:”當真理被謊言取代,所有的希望都將灰飛煙滅。”
台灣政治,我無言了。對於那些口舌伶巧、利慾薰心、行事不擇手段的綠油油生物,我只有一個恨字。我常納悶,這些人為惡究竟有沒有個極限?到底有沒有什麼惡事是他們無論有多大的私利都不會願意去做的?有沒有什麼謊言是他們無論如何都說不出口的?
對於這個同樣綠油油、低能敗德、喧囂虛榮的恐怖社會,我亦無話可說,由衷厭惡;只希望有生之年,能離它離得越遠越好。這既是初衷,亦是始終;人們若是那光,我寧可是那黑暗,不負同一軛。但願有一天,提到陳真,島上眾人再也無人聽聞。
至於親朋好友們,諸位心意心領,來日來世再報,就請容我繼續用自己的方式存活;無謂的議論與社交,老話一句,就請當做我已經死了,不用算我一份。題外話。
之所以上來打算說一些話,是因為看到有人轉貼林正杰。我想為死者鄭南榕說上幾句肺腑。
一,
林正杰說得沒錯,黨外時代,黨外人士普遍把鄭南榕當爪爬仔看,到處是這樣的耳語。原因無它,因為,第一,他是外省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心可誅;第二,他太敢、太衝了,百無禁忌,若不是爪爬仔,誰敢如此不要命?他們說,鄭南榕之所以敢突破各種禁忌的原因,就是要幫情治單位引蛇出洞,以便把激進的黨外人士給一網打盡。時下幾位綠營大老,當時不止一次如此跟我告誡,叫我要提防這個外省人,說鄭南榕在黨外沒什麼人脈,卻異常勇敢,一定是情治單位派來臥底釣魚的,務必小心別中計。
許多檯面人物一方面滿口 “理想”,努力煽動群眾抗爭,藉以累積所謂個人政治資源,進而名利雙收,搶得一官半職;一方面卻又經常抹黑、指控或貶損這些膽敢反抗的人。例如所謂街頭抗爭,誰敢以身試法走進禁區或跨越界線,帶頭的政治人物往往就會大喊 “大家冷靜冷靜,注意爪爬仔!這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陰謀,大家千萬不要中計。”
對於我的不滿,他們經常回應我說,你年紀小不懂事,不知政治險惡。但我看,險惡的應該是這樣一些人的心態與嘴臉,乃至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表面上說一套光鮮亮麗,滿口漂亮話,私底下卻又完全是另一種嘴臉。
二,
大約是1987年吧,鄭南榕是第一位公開喊出台獨的黨外人士。八零年代初期,台獨仍是絕對禁忌,輕則黑牢伺候,重則是會出人命的,因此,包括當今台獨急先鋒的長老教會,把台獨當聖經看,當時也都努力撇清台獨,更不用說窩囊到爆的民進黨了。那時候,社會上對民進黨稍有台獨疑慮或指控時,民進黨的典型回應往往是:”請不要污衊我們 (的愛國心),我們只是要爭民主。”
在這樣一種恐怖氛圍底下,鄭南榕卻公開在演講台上喊出:”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那時候,我雖是大學生,但同時也在黨外雜誌社工作,黨外圈內立即一片耳語抹黑與嘲笑。有些政治檯面人物後來裝模作樣地對鄭南榕造神、紀念、感念等等,其實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他們說鄭是爪爬仔,要不就說他腦袋進水,秀逗了,所以才不要命了;講起他可能秀逗,有幾位大老 (姑隱其名) 當時還當我的面講得樂不可支,把鄭南榕當成笑話看,當成人格異常或腦袋有洞的人那樣嘲笑取樂。
幾個月後,在一次史無前例的校園抗爭集會演講中,我無預警地站上講台,學著鄭南榕的口吻說:”請台下的情治人員準備好你的錄音機,因為我接下來要講一些重要的話”,然後我就講說:”我叫陳真,我主張台灣獨立”。話一講完,一同發起這次抗爭集會的同學有人馬上在後台大喊說 “完蛋了!陳真失控了!” “趕快把他拉下來。”。
那天集會後,我恍恍惚惚走路回我租來的住處,腦袋一片空白,沒什麼特別的情緒,就只是零零碎碎地想到自己長年在校園裏四面楚歌百般誤解的孤單痛苦,幾乎所有人把我當成暴力陰謀份子看;慢慢有了幾位同志,現在自己卻又幹出自我毀滅的事,想到前方路途艱難,感覺人生渺茫。
隔天,吃完午飯回來,我住的房間被人闖入,翻箱倒櫃,大肆破壞,而且還打傷我收養的兩條狗。接著連續幾天,發現有兩輛 “休旅車” 毫無原由地總在我後面亦步亦趨地跟著,晚上就在樓下守夜,似乎刻意要讓我知道我被釘梢跟蹤。我問一位跟李敖一起坐過牢的前輩這是在幹啥,他說這是要逮人的前兆,防止你跑了。當然,我後來什麼事也沒有,真正因為台獨而被以 “煽惑內亂罪” 移送是一兩年後 (1989年) 的事了,那是另外一些活動所致。
在這不久之後,我也離開了黨外雜誌社。離開之前,倒也經歷了跟鄭南榕類似的抹黑,圈子裏開始有人說我是國民黨派來臥底的,所以才會如此不要命。我的部份沒什麼公眾意義,不值得議論,只是讓我很訝異的是,後來,幾位相關人士跟我透露內情說,散播這個抹黑謠言的人竟然是國民黨的一位職業學生,真正的爪爬仔。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位特務學生,竟然被某本所謂學運的書抬舉成為學運領袖!媽的,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不過,媒體要捧誰貶誰,其實都是可以料想得到的。這類事情陰暗複雜,難以三言兩語說清,略過不表。
三,
林正杰說,鄭南榕 “只不過” 刊登了 “許世楷的 [ 台灣國憲法],說穿了,爭取雜誌發行量”。
這話絕非事實。如前所說,台獨在那時候是非常恐怖的禁忌,連提都不能提。不信的話,我舉個例,各位不妨去找出江蓋世的 “台獨行軍” 報導。我參加過幾次,每次都是小貓兩三隻,不是形容詞,就真的只有寥寥幾人。原因無它,因為台獨在當時是絕對禁忌。對於江蓋世的 “台獨行軍”,除了民眾日報及自立晚報,其它報紙不可能敢報導。當時言論尺度最勇猛的當然就是民眾日報,但是,當它刊出遊行布條的照片時,那張照片竟然把布條上的幾個字給抹除了,原本寫著 “台灣人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台灣獨立” 四個字不見了,變成 “台灣人有主張____的自由”。
江蓋世的 “台獨行軍,基本上是強調台獨理應是一種言論自由,不應繩之以法,不應妖魔化。這樣一種訴求尚且如此恐怖犯大忌,更不用說刊載留日學者許世楷的 “台灣新憲法草案” (不是什麼 “台灣國憲法”),那等於是不僅 “主張台獨” (而不是僅僅強調其言論自由),而且還 “著手實行台獨”。依這罪名,至少十幾年重罪絕對免不了。因此,這樣的行為絕對不只是林正杰講的 “只不過是刊登了” 什麼 “而已”。更不可能會有人為了衝雜誌業績想賺錢而寧可讓自己去坐一輩子的黑牢,會有這麼笨的商人嗎?把鄭南榕說成是一個想爭取雜誌發行量才高喊台獨者,這樣一種人格指控很不應該,因為它根本不是事實。
四,
時空不同,意義不同,你現在覺得”沒什麼”、覺得 “只不過什麼而已” 的事,在另一個時空下卻有可能得人頭落地。
舉個例: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是1986年5月19號的 “519反戒嚴綠色行動”,就是鄭南榕所發起,揚言要到總統府抗議。依戒嚴法,聚眾抗爭是唯一死刑罪,更不用說還膽敢到蔣經國統治下的總統府抗議,那簡直是不要命了,那差不多就等於是時下北韓人說要去找金正恩抗議一樣。
我也參加了這次反戒嚴活動,而那卻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同時也是唯一一次寫下遺書,因為我覺得此行後果難料,氣氛太恐怖了,很難全身而退。戒嚴令底下,誰知道參與者下場將如何?當時,開槍鎮壓的傳言四起。就我所知,劉峰松那次也寫下遺書,做好一去不回的打算。
記得那天半夜兩點,在高雄的三鳳宮前廣場集合,坐大巴士北上。黃昭輝是我們這輛車的帶頭者,他一路上教導大家若遇到鎮壓或開槍時應如何應變,應如何保護好頭部等等。我無心聆聽,光看著窗外發呆,看著黑夜中迅速往後拋去的樹影,心裏說不上害怕,只覺得茫然,孤獨,一種恍如隔世的時空異樣感。
活動前幾天,警備總部找我約談,威脅利誘,希望我不要參加。517 那一天晚上,有一位在228事變中幾乎被滅門、死了幾位叔叔伯伯包括自己父親的受難者家屬,得知我將參加的消息,竟連夜從中北部跑來高雄找我,要我打消念頭,因為他似乎相信我將一去不回。他說,我這一去,人生前途就註定毀了。我說我心意已決。
這個例子只是要說,這個年代 “沒什麼” 的舉動,在另一個時空下卻很可能致命。
五,
很多人不喜歡鄭南榕,因為老臭著一張臉。老實說,我也不是很喜歡他,我不是很喜歡具有使命感的人。我喜歡柔,不喜歡剛,喜歡柔情,勝於俠骨,當然,兩者能兼具最好。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歡鄭南榕,你都不能否認他過人的勇氣以及重大貢獻。林正杰說鄭南榕是一個彷彿無足輕重的 “黨外邊緣人”,這話完全不是事實。鄭南榕在言論自由以及在集會結社自由等等方面都是開創者。在這島上,甚至可以這麼說,自由簡直就是由他而誕生。如果連鄭南榕都只是黨外無足輕重的 “邊緣人”,那麼,我敢說,黨外幾乎所有人就根本連個屁也不是了。
一個人的某種公眾意義,當然不是看他的權位高低或當下知名度,而是看他的言行長久之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如今世人都知道蘇格拉底,但誰還會記得當年判他死刑、那些位高權重的達官貴人?
六,
黨外那年代,所謂 “同志”,往往一個比一個窩囊,空話滿天飛,很少有像鄭南榕這樣言行一致而且勇於執行的人,硬是給高壓統治下的台灣,打開一片自由天地。就連向來自大的李敖都曾說,當鄭南榕找他辦雜誌時,一來就說要 “爭取100% 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創辦的 “時代雜誌” 口號)。李敖說他聽了心裏想,也許爭取個5%、8%的言論自由吧,這小子竟有雄心說要爭取100%。
當時黨外雜誌一大堆,絕大多數品質很差,甚至存心造謠胡扯衝業績賺錢,但是,鄭南榕的 “時代雜誌” 肯定是當時所有黨外雜誌水平最高的。當時所有黨外雜誌,我幾乎每一期每一本全都看過。依我看,沒有一本雜誌的言論品質及突破禁忌等等方面能比得上鄭南榕的 “時代雜誌”。他不但罵國民黨,連蔣家也敢罵,對於同志照樣不假辭色,是一本在真正意義上具有一定是非標準與批判能力的刊物。黨外的民代及大小政客,鄭南榕的 “時代雜誌” 更是照樣批評。
有個小趣聞,不妨一提。我曾提起羅文嘉等人當年在台大的所謂 “學運”。當年各校的許多所謂 “學運” 是會笑掉人家大牙的,對外的標準台詞往往是:”我們很清純哦,我們不談政治哦,我們只談校園民主”。我在1988年自立早報創刊時寫過一些文章,批評這類所謂 “不談政治、只談校園民主” 的 “清純學運”,我說,校園哪有什麼民不民主的問題?那些什麼 “學生會普選” 的議題本身無甚意義,唯有當社會整體民主化,校園自然就會有它該有的自由空氣;撇清政治只是一種懦弱的藉口,無關乎什麼清不清純。
記得當時羅文嘉他們在台大不知道弄了一個什麼活動,鄭南榕在雜誌上報導了這件事,結果這些清純的學運領袖們竟然寫信來雜誌社抗議,威脅往後不得再 “擅自” 報導,否則將切斷一切連繫云云。鄭南榕公開寫了篇文章回應說,我們連軍警特的威脅都不怕,怎麼會怕你們連不連繫?文章標題是:”敢做就不要當縮頭烏龜”。
七,
林正杰說,鄭南榕當時 “孤家寡人,財務吃緊”,所以才來辦雜誌,簡單說就是為了錢。但這不是事實。其它大部份黨外雜誌為了賺錢,確實如此亂搞,但鄭南榕是在賣命玩命,絕不是為錢。他連命都不要,怎麼會只是為了錢?而且,他也不是 “孤家寡人”,那時他女兒鄭竹梅恐怕都已經念小學了,怎麼會孤家寡人?你認不認同他的思想是一回事,但若說他辦雜誌或政治言論不設限是因為”財務吃緊” 想賺錢,那既不是事實,更不厚道,可以說就是人格抹黑。
八,
林正杰說,鄭南榕被判刑後 “很害怕”。我想請問,他連死都不怕,他還怕什麼?他如果害怕,乖乖配合國民黨、痛改前非,不就一切沒事了?甚至還能因此吃香喝辣不是嗎 (就如同這年頭大家爭相在言行上跟綠營拉上關係一樣),何必拋妻棄女選擇自焚?而且,自焚是所有自殺行為中,致死率最高同時也是痛苦指數最高的一種方法。
林正杰還說,鄭揚言自焚到真的自焚之間有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卻沒有一個 “真正的朋友” 來把他辦公桌下的汽油桶拿走。我不知道這段話是要暗示什麼。鄭南榕個性剛烈,別說朋友,就算是太太葉菊蘭也不敢把那桶汽油拿走。
鄭南榕宣布要以死相抗後,在雜誌社自囚了 71天 (不是林正杰說的一兩星期,而是兩個多月)。吃喝睡完全都在雜誌社裏頭,等待國民黨的拘提。他自囚期間,一些黨外人士輪班去保護他。當他宣布 “over my dead body” (抵死不從) 時,我那時候正在籌組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同樣搞得政治上滿城風雨,因為兒童人權在當時也犯大忌。”人權” 兩個字都不允許你提了,你還講 “兒童人權”,豈不是要自討苦吃。我當時發表一篇台灣兒童人權報告,在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 得獎,還被聯合國的一篇報告所引用,國民黨認為我詆毀了黨國的美好形象。1989年4月4日兒童節,我發起示威遊行,擔任總指揮,要求開辦兒童醫療保險以及五歲以下重症兒童免費醫療。
當時,有個女學生跑來找我,說想邀我一起去時代雜誌社輪班,阻止國民黨來抓鄭南榕。我說好,但我說我得先忙完這場兒童節示威後再說。當時參與遊行的群眾約50幾人,一路上荷槍實彈的警察、便衣特務卻高達兩百多人。抗爭結束後,那個女學生又打電話來,約好過兩天就去雜誌社,輪班保護鄭南榕,防止悲劇發生。沒想到,兩天後,4月7號那一天,一堆電話就響了,說鄭南榕自焚了。
我要說的是,就算我去到現場輪班,我也不可能把他的汽油桶拿走,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內心希望他死,也不意味著我們只是在利用他。
九,
把鄭南榕說成 “害怕” 被判刑、說成財務不佳想靠火辣言論賺錢,這完全不是事實。
我常跟人提起一件事,這事是劉峰松老師跟我說的。他說他去探望鄭南榕,希望他不要有過激反應。劉峰松說,鄭南榕卻告訴他,國民黨長年以來抓人關人殺人,以為大家會怕。鄭南榕用台語說,”國民黨這一招,到我鄭南榕這裏就要給我擋下來”,意思是說,這一招對我鄭南榕是行不通的,這一招到我這裏就失效了,因為我根本不怕死,於是也才有後來 “over my dead body” 那句話,表示抵死不從,絕不會被逮捕的決心。鄭南榕說,”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絕不會抓到我的人”。
我常想起那天晚上在路邊一個賣豆花的攤位上,劉峰松見完鄭南榕之後跟我說的這句話。劉老師邊說邊學著鄭南榕比手勢,在肚子前比出 “給我擋下來” 的手勢,讓我印象很深。總之,鄭南榕不是那種講空話的人,他說要死,就一定會尋死。
十,
林正杰倒是說對了一件事,鄭南榕不一定是個具有充份台獨熱情的人。
他的死,具有充份的自主意識,不是糊里糊塗的死,而是自囚在雜誌社 71 天之後的一種有意識的慘烈行動。鄭南榕念過哲學系,他在日記本上曾寫著一句話:”當哲學家被處死,山河都將流淚。” 我知道他是嚮往某種精神世界的,但這個精神世界並不是台獨。以台獨來消費他,其實對他只是一種醜化和貶低。任何一個嚴肅的哲學家,都不應該為任何一種特定主張而死,因為就如羅素所說,任何特定主張均非永恆或普世之物,而是隨時空而變;哲學家應該不至於蠢到或庸俗到為此而死才對。
我不敢對別人的精神世界任意指指點點,但我相信,鄭南榕並不笨,他就算要死,也該為一種比個人生命更長久更永恆的基本價值或情感,而絕不會是為了一時一地的特定政治主張。
十一,
絕大部份人應該都不知道,其實鄭南榕剛自焚那幾天,民進黨很多人是根本不相信的,他們一口咬定鄭是被國民黨 “先活活打死之後再放火焚屍",甚至還有人指證歷歷說他親眼看到屍體被移動,非原始現場。當時有一位與我熟識的大老還因此發起抗爭,要求國民黨殺人凶手公布真相。總之,他們先是生前抹黑說鄭南榕是特務,死後卻又說他不可能自焚,一定是被萬惡的國民黨給活活打死,並說他被火燒掉的一截小腿就是為了企圖凐滅證據云云。
自焚後,陳菊去探望鄭的太太葉菊蘭和女兒鄭竹梅。我跟陳菊一道去,聽葉菊蘭談起幾位綠營大老送輓聯鮮花來,葉說,她故意把這些輓聯鮮花塞到後面讓人看不到,意思是說這些人虛情假意,令她不齒。
十二,
林正杰還講對了一件事,他說,鄭南榕 “生前黨外避之唯恐不及,死後大家都假惺惺鞠躬,盡情消費,真是虛偽。” 不但虛偽,而且齷齪下流,拿來當成一種政治工具儘情操弄。
每次來到台南市政府附近吃飯,看到那條什麼 “南榕大道” 就 x 它媽的很想吐。成大也是,一群綠油油的學生,氣燄高張地搞個什麼 “南榕廣場”。我當然不會反對給他設個銅像啦或以之命名啦什麼的,我只是太了解眼前這一切所謂 “紀念” 裏頭的政治操弄,把一個好好的人,理應屬於所有人的死者,把他理應為人類所共同尊崇的某種精神自由、情感與價值,給拿來像廁紙那樣進行無恥齷齪的政治操弄,甚至矮化成什麼台獨建國烈士。光是為了一個什麼統獨就拋妻棄女、要死要活的,鄭南榕會是這麼眼光短淺思想淺薄的人嗎?我不相信。
一群人,之所以紀念某個人,理應是因為這群人同樣嚮往或甚至具有某種與其紀念對象類似的特質或精神價值才對,但你看,時下這些努力消費鄭南榕的人,不管老的少的,一個比一個恐怖,恰恰是那種與自由精神強烈背道而馳的人,往往非常右,非常種族主義,仇中與臺獨幾乎就是他們的唯一價值,而且,凡是不認同者就是敵人,對之就要打,就要鬥,就要抹黑。我真不知道這些混蛋究竟是在紀念什麼。這些人應該紀念比方說挪威殺人魔或江青四人幫與紅衛兵等等之類的人才對,因為雙方屬性比較接近。
十三,
鄭自囚期間,有人給他拍了一張照片,他躺在雜誌社沙發上睡覺,眼鏡摘掉放在一旁;也許因為天氣冷,那天他睡覺時就一隻手不自主地伸入衣領裏頭取暖。我給這張照片放大,還做了護貝,當我剛當上主治醫師首度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時,我就隨手把它貼在書桌前的牆壁上。然而,現在就算你給我一百萬,要我再把它貼在辦公室裏,我絕不肯,因為我不想讓人誤以為我跟時下這批綠油油的混蛋是同一類的人。
十四,
鄭南榕是1989年4月7號自焚。一個月後的5月19號,民進黨發起送葬遊行,途經總統府抗議。我的好朋友詹益樺,跟我走在一塊,快接近總統府時,我看他把手上的一些東西交給一輛宣傳車上的人,然後突然衝向總統府的鐵蒺藜,引火自焚,同時還朝總統府方向丟出一本聖經。我和戴振耀、尤宏及楊秋興等人,一起把他送往台大醫院,但他其實在運送過程中就斷氣了。我在他自焚的地方,撿到他引火的打火機,隨手就放進口袋,想留個紀念,但後來想,國民黨也許會嫁禍,所以當我從太平間又返回總統府抗爭現場時,就把那個千輝牌打火機又丟回原地。
跟鄭南榕一樣,詹益樺同樣也值得紀念。他之前跑船,打零工,不能算是讀書人,但他對知識、對所謂真理與神乃至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善意與情感,卻有著一種很強烈的傾向,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愛慕。他外表粗獷,但說起話來卻輕聲細語的,像個姑娘在說愛,頗似其內心之細膩溫柔。我曾給他寫了篇悼文,標題稱他為一個虔誠的慕道者。他也許沒法像所謂知識份子那樣能夠把道理講得神靈活現,但我深知其心之赤忱。
跟鄭南榕一樣,拿詹益樺來消費,刻意捧成某種政黨立場的代言人或某種政治主張的烈士,那真是很卑劣的一種行為。這些抬舉者、消費者,並不是真的看重什麼普世永恆的人類精神價值與情感,而只是看重選票,看重顏色,看重特定政治主張 (即台獨),藉以攻擊異己。
十五,
不管是鄭南榕或詹益樺,我知道的事還很多,但我能說的卻很有限,特別是詹益樺;並不光是考慮該說或不該說,而是說不說得出來的問題,生命畢竟不是是非題或選擇題,它像一道風景,一首曲子,你得有詩人一般的本事,或許才說得清以命相許究竟何物。唯一能確定的是,那樣的人,那樣的生命,不會單單許給一種政治主張那般廉價。
詹益樺原本跑船,在一次船難中在荷蘭被救起,受到異鄉人細心無私的照料,使他開始對美好社會以及人與之間無私的善意產生憧憬,開始投入社會與政治改革….這段往事,可以當成我想說卻無能說上的這故事的開頭,於是故事自然就也只能講到這裏,成為它的結尾。
陳真 2015.08.02.